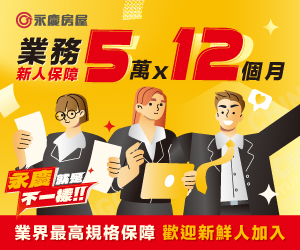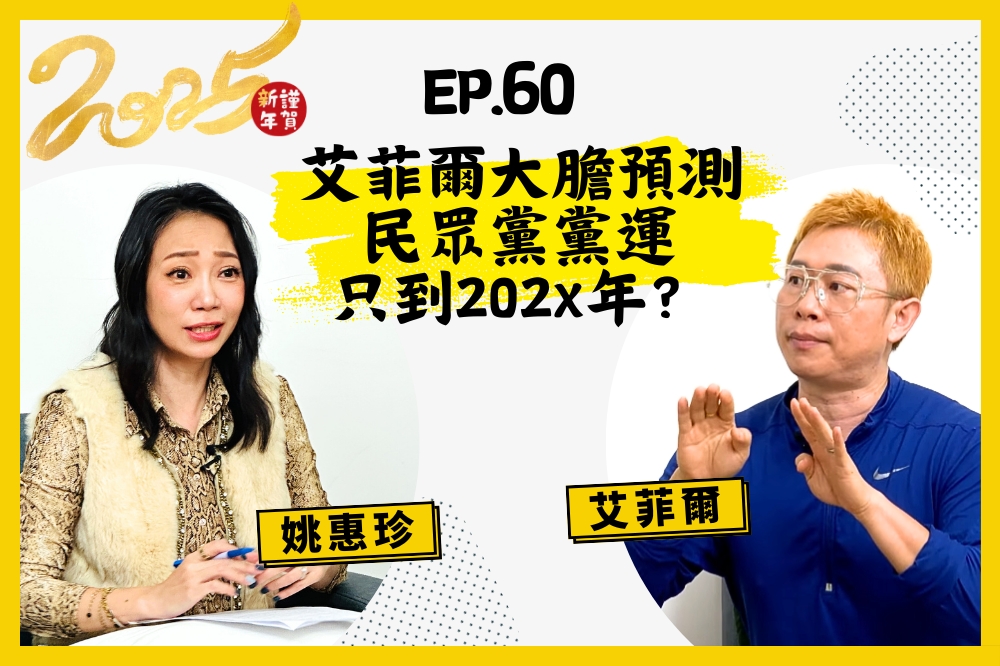上報 Up Media
toggle- 最新消息 民進黨控藍白「親中毀台」刪國防 民眾黨團回嗆:胡言亂語 2025-05-12 22:40
- 最新消息 三聯集團負責人徐少東吸金22億遭判12年 驚傳人間蒸發家屬急報案 2025-05-12 22:15
- 最新消息 日本連續發生少年殺人釀3死 一起疑無差別攻擊 2025-05-12 21:58
- 最新消息 吳思瑤用「性侵」比喻憲訴法三讀過程 陳智菡嗆:能不能別這麼噁心 2025-05-12 21:55
- 最新消息 美中談妥關稅降幅 貝森特稱鋼鐵、晶片供應鏈去中化更進一步 2025-05-12 21:35
- 最新消息 林月琴曾任「凱凱案」外聘督導 議員爆:鐘點及出席費恐破百萬 2025-05-12 21:33
- 最新消息 年輕人也超愛「粉紅超跑」 外媒揭白沙屯媽祖信眾暴增原因 2025-05-12 21:13
- 最新消息 台南8連霸議員涉詐助理費533萬 遭判2年獲緩刑 2025-05-12 20:48
- 最新消息 苗栗鐵板啃不動! 藍委陳超明、邱鎮軍二階連署未達標 2025-05-12 20:22
- 最新消息 好酸!轉發「旗魚人口」梗圖 饒慶鈴:謝謝行政院推廣台東漁產 2025-05-12 20:08

將民進黨比喻為納粹、法西斯,是統派從「塔綠班」、「綠共」開始,一連串意圖將民主虛無化的對內宣傳話術。(攝影:王侑聖)
我認為把「綠粹」單純解讀為中國合理化入侵台灣的藉口,似乎偏移了重點。
這些話是說給誰聽的?中國嗎?中國長久以來的內宣外宣,一貫以其單方面的「主權」解讀為基礎,例如五月七日習近平訪俄時又再次表示:「《開羅宣言》、《波茨坦公告》等一系列具有國際法效力的文件都確認了中國對台灣的主權,其歷史和法理事實不容置疑,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的權威性不容挑戰。」在此之上添加「反納粹」,必要性不高,也與台海歷史脈絡不符。
說給國際社會聽嗎?首先,「反納粹」從未「合理化」俄國對烏克蘭的出兵;再者,在台灣提出這種缺乏歷史常識與歷史敏感度的離譜指控,只會被國際上所有明眼人打臉,就像現在這樣。
我認為將民進黨比喻為納粹、法西斯,是統派從「塔綠班」、「綠共」開始,一連串意圖將民主虛無化的對內宣傳話術,藉此瓦解民眾對民主制度的信心。這比起一個沒人相信的出兵藉口,還更加可怕。
只要不是完全只看俄媒敘事的人都清楚,「烏克蘭新納粹坐大」根本毫無根據。確實,在烏克蘭的反俄自願軍中有部分激進的烏克蘭國族主義者,包括極右翼/新納粹分子,但極右黨派在烏克蘭政壇一直處於邊緣地位,難以成氣候。
目前極右翼在歐洲支持率普遍上升,不少國家都有泛極右政黨進入國會,然而烏克蘭是極右翼支持率最低的歐洲國家之一,比瑞典、荷蘭、法國都低很多。
對普丁而言,一支反俄自願軍中的一部分新納粹成員為他提供了藉口。他可以將所有反俄意識貼上「納粹」標籤,再用「去納粹化」作為出兵名義。
「去納粹化」這個詞源於納粹德國戰敗後,同盟國在德國進行清除納粹影響的歷史術語,聽起來非常正面,也與俄羅斯歷史上的「光榮時刻」連結。
然而從1930年代到二戰期間,納粹德國與蘇聯這兩個暴政血洗大地,東歐民眾長年遭受雙方摧殘,深知兩者皆非善類。將「反俄」等同於「萬惡的納粹」,再用「去納粹化」來自圓其說,這種說法只有在俄國才會引起共鳴,對其他人來說都是荒誕至極。
事實上,今天的俄國與中國主流政權,本身就展現出許多極右特質:帝國主義、國家主義、威權統治、仇視性少數等等。真要說極右政權,無人能出其右。此外,俄國國內也確實存在不少極右/新納粹團體。
重點是,就算今天烏克蘭真的「新納粹坐大」,也絕不構成俄國全面侵略的理由,這始終只是說給支持者聽的一套說詞,從來沒有「合理化」或「正當化」過任何行為。
普丁的強人作風與大俄羅斯主義非常契合中共主旋律,在俄烏戰爭的敘事上,中共自然樂於迎合普丁。
但就我接觸到的挺俄中國人來說,我感覺他們其實並不在乎烏克蘭納不納粹。「前妻躺在別人懷裡,還跟別人聯手欺負前夫,該打!」這種說法反而更能打動他們。相較於東歐,「反納粹」這個詞在台海沒有什麼歷史共鳴。反而像「日本皇民」、「美帝兒子」這類說法還更容易操作。
所以,說「綠粹」是「為中國出兵鋪路」,有點說不太通。
統派本來就不太在意民主,他們長期將各種極權詞彙套用在民進黨身上,這種操作並不是要針砭民進黨「不夠民主」,而是試圖營造出「民主不可信」這種虛無印象。這類話術主要不是說給外人聽的,而是內部宣傳。
朱立倫說民進黨在像納粹、法西斯那樣攔截民主,表面上看似為民主發聲,但實際上這種毫無歷史常識與歷史敏感度的民粹言論,是對台灣民主的全面否定。它暗示民主法治遭到顛覆,並指涉民主導致混亂、削弱法治程序的可信度。
這也與中俄多年來積極營造的「西方民主虛無與敗退論」不謀而合。例如目前歐洲極右/新納粹勢力的重起,就常被中俄誇大作為西方民主敗退的證據。
許多海外中國人也會相信這一套。例如當他們在瑞典遇到任何制度缺陷或與自身期待不符時,常會笑譏:「瑞典不是說自己很民主嗎?結果也只是表面罷了。」這類淺碟的理解,也凸顯了對民主法治的根本誤解。
就台灣而言,「綠粹」、「塔綠班」這些用語,代表著民主虛無論與民主敗退論的巨大隱憂。與此對抗,我們必須持續、耐心地溝通民主與法治社會的程序、意義與價值。(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/作者為作家,現居瑞典)
熱門影音
熱門新聞
- 【5月母親節優惠】星巴克買一送一!四大超商、CoCo、清心、麻古茶坊等 18 家手搖飲咖啡冰品優惠懶人包
- 美證實中國殲-10擊落法製飆風 殲-10搭PL-15飛彈戰力恐改西方台海及印太部署
- 吳磊新劇擠下《蓮花樓》成毅奪男主 三搭《偷偷藏不住》趙露思破局內幕曝光
- 《難哄》章若楠爆秘戀白敬亭偷曬恩愛 她PO出愛犬自拍卻放「這物品」全網秒懂
- 《難哄》白敬亭與章若楠爆秘戀 緋聞女友宋軼現身機場與他「3穿搭元素」相同挨轟蹭流量
- 【有片】李芷霖否認當小三 正宮拿「吃小頭」影片再嗆:有妳的臉和聲音
- 【獨家】中科院銳鳶二型無人機爆國安問題 通訊模組竟藏中國晶片
- 【母親節優惠】一条通限時五天半價優惠只要 20 元!三重「這兩間」門市慶開幕送現金券、指定品項半價連續四週